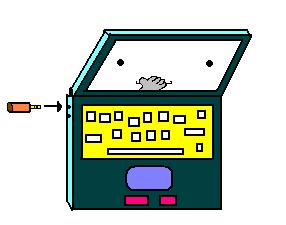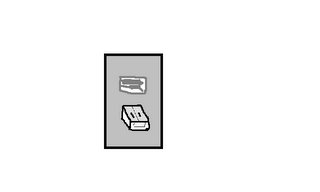司令台上有個壯年男子在表演。他拿著是一雙水管改造成的鼓棒,敲打的是鋼鐵做成的方鼓,每個鼓又連結了震動感測器,把每一下震動換成聲音,透過電腦放出來。兩旁是一整櫃的電腦和效果器。
舞台後方是用許多垂直鐵管做成的豎琴,前方是像垃圾回收子車的東西,敲擊他的邊卻會發出類似吉他絃的聲音。男子把水管拿成匹克的樣子,對著那個邊用泛音。連結線接觸不良,一下子發出咚咚的聲音,一下子發出高頻的聲音。
所有的設備都相連成一個巨大活動式的機器,像是電子花車那樣,甚至還連結了賣耳環的攤販推車、投零錢的夜市彈珠台等等。越裡面的設備越高,一看竟然也有人在買東西,他手上的零錢掉了下來,大約是二樓的高度。我把錢丟回去給他們。
Friday, December 29, 2006
Tuesday, December 26, 2006
PRESS (4)
凌晨三點,他仍守在工作台前不願休息。嗶,嗶,嗶,窗外小巷響起卡車的倒車聲,魚市場也開始進貨了。嗶,嗶,嗶,許多白滑冰冷的魚拍動胸鰭划過他的鼻頭,眼前的草稿紙漸漸濕黏起來,散發出海的鹹腥味。他靜靜聽著魚販吆喝殺價的聲音,腦海裡浮現了一顆顆反光的魚眼,那是牠們降生入水便不曾闔上的,尤其在面對死亡時更是奮力睜大,睜的都出血了。
當他小時候第一次把臉貼在海產餐廳的水族箱玻璃板上,領悟到那些蒸熟的眼睛打從開始就沒有閉上過,看著自己脫離水面,看著鍋鏟與薑片,也看著他的眼睛,他便一直嚮往這種生存。
他起身在房間裡轉了轉,不小心還撞到幾條紅鯛。出門透透氣吧,靈感不在身邊的時候,必定是跑上街了。
街燈總是有幾盞不亮。亮的幾盞,飛繞著許多蟲蛾,嗤嗤作響。漫步經過幾個路口,冬天的世界仍是黑悶悶一片。到了天橋下,賣茶葉蛋的老伯已經燒著了他的鐵製小圓爐,陣陣茶香趕去了魚腥味。老伯的露天店面和天橋下幾十年來待拆的違建一樣從未改變,而他駝著背煮蛋的影子似乎也刻印在身後的綠色圍籬板上,像一幅憤世青年的噴漆。
「要幾個?」
「一個就好。」
老伯翻開黃頁電話簿,選了一張撕下,沿對角線對摺再彎成錐型一手握著,另一手拿著鐵網勺子在茶汁裡攪了幾下,好不容易挑中一個小心翼翼的放進紙包,將多餘的反摺下來,遞給他。他接過溫熱的茶葉蛋,跟老伯道了聲謝。老伯對他點點頭,眼睛閃著棕色的光芒。
回程他又經過了魚市場。許多魚已被刮除鱗片切去內臟,赤裸的攤在冰塊裡。
坐在桌前,他十分笨拙的剝著茶葉蛋,指甲都染了色。剝蛋殼和刮魚鱗都是麻煩事,不論怎麼弄總都會殘留一小片。他一面嚼著,一面拿起堆在角落的鋁片鋪在地上,想像著牙膏罐完成的樣子。躺上銀色的鋁床,他感到混身冰冷,好像被去了鱗的魚。
天邊漸漸轉亮,空氣中的魚腥味已經淡去,只剩草稿紙濕了一角。
當他小時候第一次把臉貼在海產餐廳的水族箱玻璃板上,領悟到那些蒸熟的眼睛打從開始就沒有閉上過,看著自己脫離水面,看著鍋鏟與薑片,也看著他的眼睛,他便一直嚮往這種生存。
他起身在房間裡轉了轉,不小心還撞到幾條紅鯛。出門透透氣吧,靈感不在身邊的時候,必定是跑上街了。
街燈總是有幾盞不亮。亮的幾盞,飛繞著許多蟲蛾,嗤嗤作響。漫步經過幾個路口,冬天的世界仍是黑悶悶一片。到了天橋下,賣茶葉蛋的老伯已經燒著了他的鐵製小圓爐,陣陣茶香趕去了魚腥味。老伯的露天店面和天橋下幾十年來待拆的違建一樣從未改變,而他駝著背煮蛋的影子似乎也刻印在身後的綠色圍籬板上,像一幅憤世青年的噴漆。
「要幾個?」
「一個就好。」
老伯翻開黃頁電話簿,選了一張撕下,沿對角線對摺再彎成錐型一手握著,另一手拿著鐵網勺子在茶汁裡攪了幾下,好不容易挑中一個小心翼翼的放進紙包,將多餘的反摺下來,遞給他。他接過溫熱的茶葉蛋,跟老伯道了聲謝。老伯對他點點頭,眼睛閃著棕色的光芒。
回程他又經過了魚市場。許多魚已被刮除鱗片切去內臟,赤裸的攤在冰塊裡。
坐在桌前,他十分笨拙的剝著茶葉蛋,指甲都染了色。剝蛋殼和刮魚鱗都是麻煩事,不論怎麼弄總都會殘留一小片。他一面嚼著,一面拿起堆在角落的鋁片鋪在地上,想像著牙膏罐完成的樣子。躺上銀色的鋁床,他感到混身冰冷,好像被去了鱗的魚。
天邊漸漸轉亮,空氣中的魚腥味已經淡去,只剩草稿紙濕了一角。
Monday, December 25, 2006
Sunday, December 24, 2006
Saturday, December 23, 2006
寂寞的專家
「人生很快就過去了。」
-木魚,袁哲生
袁哲生,或許在大眾的印象中,是那個得過許多文學大獎、未來一片光明,卻在三十八歲便自我了斷的作家,總是在提到痛失英才之類的話題時會被拿出來涕泗縱橫一番。看過他的文章之後,我想那樣的結局對他是一種必然。
最早讀到他的文章,是聯合文學上的「父親的輪廓」,裡面寫著他和他父親的互動,直到父母離異,聽聞到父親過逝的訊息,而他大半都以聽覺來描寫父親,取名為輪廓更是富有意境。他的父親在家裡的角色是處於溫和、被動、不知所措的,這樣的父親形象在我成長經驗中是極常見的,因此感到非常親切。袁哲生描寫的核心總是圍繞著「人孤單的降生世上,最後終要回歸死亡」,這麼沉重但一般人總是隱諱不提的事實,如何在其中存活著,不論是某一天雷擊似的驚悟,在現實中掙扎著,或是刻意遺忘,以及許多失去或擁有的種種。他的筆法敏銳細膩,使用的比喻充滿靈性,常能超脫時空進入意識幻想,但是他總是寂寞的站在遠處,保持著距離感,即使我們讀著他的文字非常感動而起身尋找,他也早就不在那裡了。確實,現在他也不在了。
「寂寞的遊戲」是聯文出版的,放在西門誠品最下一排。薄薄的一本,一天只能看20頁,否則一個晚上就看完這麼美好的文字會有強烈的失落感。或許點到為止充滿餘韻的短篇比較適合他這樣敏感的作家,不過「木魚」這篇就是較長的作品,而木魚這樣富音韻的形象也在文字間不斷的響著。當他處理著沉重的課題,又以細密的長篇來開展時,總是令人一面閱讀著一面擔心受怕,深怕最後一點自我安慰的欺騙也被揭開了。
袁哲生不斷的以最輕靈的筆調,挑動人生最沉重的課題。我想他從不打算說出什麼答案,他只想告訴我們寂寞的樣子。畢竟答案我們也早就知道了。
-木魚,袁哲生
袁哲生,或許在大眾的印象中,是那個得過許多文學大獎、未來一片光明,卻在三十八歲便自我了斷的作家,總是在提到痛失英才之類的話題時會被拿出來涕泗縱橫一番。看過他的文章之後,我想那樣的結局對他是一種必然。
最早讀到他的文章,是聯合文學上的「父親的輪廓」,裡面寫著他和他父親的互動,直到父母離異,聽聞到父親過逝的訊息,而他大半都以聽覺來描寫父親,取名為輪廓更是富有意境。他的父親在家裡的角色是處於溫和、被動、不知所措的,這樣的父親形象在我成長經驗中是極常見的,因此感到非常親切。袁哲生描寫的核心總是圍繞著「人孤單的降生世上,最後終要回歸死亡」,這麼沉重但一般人總是隱諱不提的事實,如何在其中存活著,不論是某一天雷擊似的驚悟,在現實中掙扎著,或是刻意遺忘,以及許多失去或擁有的種種。他的筆法敏銳細膩,使用的比喻充滿靈性,常能超脫時空進入意識幻想,但是他總是寂寞的站在遠處,保持著距離感,即使我們讀著他的文字非常感動而起身尋找,他也早就不在那裡了。確實,現在他也不在了。
「寂寞的遊戲」是聯文出版的,放在西門誠品最下一排。薄薄的一本,一天只能看20頁,否則一個晚上就看完這麼美好的文字會有強烈的失落感。或許點到為止充滿餘韻的短篇比較適合他這樣敏感的作家,不過「木魚」這篇就是較長的作品,而木魚這樣富音韻的形象也在文字間不斷的響著。當他處理著沉重的課題,又以細密的長篇來開展時,總是令人一面閱讀著一面擔心受怕,深怕最後一點自我安慰的欺騙也被揭開了。
袁哲生不斷的以最輕靈的筆調,挑動人生最沉重的課題。我想他從不打算說出什麼答案,他只想告訴我們寂寞的樣子。畢竟答案我們也早就知道了。
Friday, December 15, 2006
PRESS (3)
床底下的眼睛仍然緊閉,身上穿著直條紋襯衫,樣式和我衣櫃裡的ㄧ樣。牙膏罐中段有ㄧ道深深的凹痕,似乎將他擠出開口是相當費力的事情。凹痕的後段圓圓鼓起,把末端的打褶都撐開了。我小心觀察著他,好像同時在照鏡子和參觀蠟像館,而且蠟像還有著我的面孔。
說不定真的是某位仁兄精心策畫,依我的模樣造一個假人,還大費周章藏進床底下。那麼它就是一份禮物了。這位神秘人物應該是藝術家,行為心理學家,神仙妖怪,或是深深憎恨我的人,總之是令人尊敬的行業。想到自己如此受到重視,我不禁大受感動。或許他還在對街裝了攝影機想錄下我大受驚嚇的癡傻表情(是的,從早上三樓租不出去的空房就有個光點在規律閃動,那必定是機器燈號),於是我馬上收起笑容,面對窗戶誇張的跌坐在地,以報答這份大禮。
他的皮膚質感,指甲縫裡的髒東西,都像是生命體獨有的特權,甚至連衣服上淡淡洗衣粉味道都很熟悉。唉,現代世界的真假早已難分,日本機器人偶的頭髮都會自動長長,怎麼還會有關節接縫這樣老派的破綻呢。無法期待切開自己皮膚發現裡頭溫馨的塞滿了棉花,反而可能真是鮮血直噴的場面,頓時讓人失望起來。只能看眼睛了,即使科技能夠完全模仿上帝創造人型,眼神還是它們無法征服的聖地。
於是我對他輕聲呼喚著我的名字,好像出竅靈魂首次邂逅肉體,總要忘情失態地確認是否真的掙脫了臭皮囊。只是現在的我不是以優雅姿態飄在空中,隨意穿牆偷虧鄰居生活,而是坐在地上與俗世為伍。
他沒有任何反應,似乎真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體。午休時間快結束了,我慢慢站起身,整理皺折的衣服,準備回去上班。
突然間,牙膏罐晃動了起來,發出令人不安的聲音,那雙抓著鐵環開口的手用力推著,青筋一條條鼓起。我緊張地往前走一步,他的眼睛倏地睜開,帶著原始野蠻的力量,對著我說:「推我一把」。
在那瞬間我看見運轉世界的巨大齒輪迎面而來,它的齒槽十分舒適,我一如每天早晨起床走向廁所洗臉拿起牙膏那般,無意識的往牙膏罐中間擠了下去,腦中也和每天早上一樣完全空白。
說不定真的是某位仁兄精心策畫,依我的模樣造一個假人,還大費周章藏進床底下。那麼它就是一份禮物了。這位神秘人物應該是藝術家,行為心理學家,神仙妖怪,或是深深憎恨我的人,總之是令人尊敬的行業。想到自己如此受到重視,我不禁大受感動。或許他還在對街裝了攝影機想錄下我大受驚嚇的癡傻表情(是的,從早上三樓租不出去的空房就有個光點在規律閃動,那必定是機器燈號),於是我馬上收起笑容,面對窗戶誇張的跌坐在地,以報答這份大禮。
他的皮膚質感,指甲縫裡的髒東西,都像是生命體獨有的特權,甚至連衣服上淡淡洗衣粉味道都很熟悉。唉,現代世界的真假早已難分,日本機器人偶的頭髮都會自動長長,怎麼還會有關節接縫這樣老派的破綻呢。無法期待切開自己皮膚發現裡頭溫馨的塞滿了棉花,反而可能真是鮮血直噴的場面,頓時讓人失望起來。只能看眼睛了,即使科技能夠完全模仿上帝創造人型,眼神還是它們無法征服的聖地。
於是我對他輕聲呼喚著我的名字,好像出竅靈魂首次邂逅肉體,總要忘情失態地確認是否真的掙脫了臭皮囊。只是現在的我不是以優雅姿態飄在空中,隨意穿牆偷虧鄰居生活,而是坐在地上與俗世為伍。
他沒有任何反應,似乎真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體。午休時間快結束了,我慢慢站起身,整理皺折的衣服,準備回去上班。
突然間,牙膏罐晃動了起來,發出令人不安的聲音,那雙抓著鐵環開口的手用力推著,青筋一條條鼓起。我緊張地往前走一步,他的眼睛倏地睜開,帶著原始野蠻的力量,對著我說:「推我一把」。
在那瞬間我看見運轉世界的巨大齒輪迎面而來,它的齒槽十分舒適,我一如每天早晨起床走向廁所洗臉拿起牙膏那般,無意識的往牙膏罐中間擠了下去,腦中也和每天早上一樣完全空白。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06
PRESS (2)
他彷彿又看見那個畫面模糊的閃動,像是颱風天打開電視機的灰黑雜訊,干擾著眼前的一切。當時大雨傾盆,走在地下道裡也能聽見細緻雨點織成的白色噪音,綠色磁磚牆裡水管線也共鳴著。他倒持雨傘像握著劍的刺客,專心聽著是否有任何王侯想趁雨夜遁逃。這時窩在角落的流浪漢正敲打著破爛鍋碗,那鏗鏘竟合著路人踏出的時尚節拍,他明瞭這暗號必定蘊藏人生的秘密。他也席地而坐,感受生鏽金屬與昂貴鞋跟的迴音螺旋升上一層層梯級,加入了攤販慌忙關上皮箱的聲音,加入了便利商店櫃檯不自然的歡迎語,加入了越南新娘正音班整齊的朗誦,而課室外的雨點還未斷線。正當他想譜下這獨特的歌曲,流浪漢突然猛烈的咳嗽喘息不止,向旁邊軟倒下去,沒了呼吸。路過的人們全停下腳步,像是演奏會結束起立致敬的觀眾們,若有所失地站著。
那樣激昂的場面震撼著他,好像身體被烙上一幅休止符圖案,滾燙的直發痛到心裡。他明白全世界都躲不開那樣的命運,包括他自己。
但即使如此,現在的他心中再怎麼努力默想,連呼吸都摻入這些意志,也只能微微吹動手背上的細毛。雖然今天也下著雨,電視卻沒有斷訊,甚至清楚的令人反胃。
他受困在一場公演籌備會,所有人都必須參與。他總是無法了解表達能力低落的現代人為何如此熱衷開會。為了討論出公演主題,ㄧ個又ㄧ個文藝青年登台高呼新穎構想,但在擁護者暗中較勁互相牽制下,支持者總是無法過半,氣氛停滯的連靈魂都要凝結。在漫長尖銳的話語亂流中,他即將脫口的點子也自動撤退回喉嚨,不願加入戰局。
在眾人瀕臨放棄邊緣幾乎要請神明開示,從某個角落蹦出了句簡單的話,這一刻他腦中正在設計晚餐的情節。雖然這幾個字飄散在空中,沒有劃出刺眼的火花,沒人因此大聲讚賞,它卻慢慢的,幾乎同時的降落每個人心底,帶著ㄧ種重量,像是指揮家舞動黑棒輕點著音符的力道,不管小提琴大提琴,都一致的靜下來。
"來扮牙膏怎麼樣?"
於是他開始趕工,四處採買鐵錫,鋁片,銀色顏料,準備打造一條牙膏罐。
ㄧ條和人等高的牙膏罐。
那樣激昂的場面震撼著他,好像身體被烙上一幅休止符圖案,滾燙的直發痛到心裡。他明白全世界都躲不開那樣的命運,包括他自己。
但即使如此,現在的他心中再怎麼努力默想,連呼吸都摻入這些意志,也只能微微吹動手背上的細毛。雖然今天也下著雨,電視卻沒有斷訊,甚至清楚的令人反胃。
他受困在一場公演籌備會,所有人都必須參與。他總是無法了解表達能力低落的現代人為何如此熱衷開會。為了討論出公演主題,ㄧ個又ㄧ個文藝青年登台高呼新穎構想,但在擁護者暗中較勁互相牽制下,支持者總是無法過半,氣氛停滯的連靈魂都要凝結。在漫長尖銳的話語亂流中,他即將脫口的點子也自動撤退回喉嚨,不願加入戰局。
在眾人瀕臨放棄邊緣幾乎要請神明開示,從某個角落蹦出了句簡單的話,這一刻他腦中正在設計晚餐的情節。雖然這幾個字飄散在空中,沒有劃出刺眼的火花,沒人因此大聲讚賞,它卻慢慢的,幾乎同時的降落每個人心底,帶著ㄧ種重量,像是指揮家舞動黑棒輕點著音符的力道,不管小提琴大提琴,都一致的靜下來。
"來扮牙膏怎麼樣?"
於是他開始趕工,四處採買鐵錫,鋁片,銀色顏料,準備打造一條牙膏罐。
ㄧ條和人等高的牙膏罐。
Monday, December 11, 2006
PRESS (1)
早上,當遲鈍的雙腳尋找拖鞋時,踢到了某樣東西。長長的一條躺在床底下,還在繼續賴床。
它的形狀就像大型牙膏罐,只是蓋子不見了。裸露的鐵錫開口,飄散出的不是亮白薄菏味或三色彩虹,而是圓圓的黑色物體。近看,原來是一顆頭。一顆有著和我一模一樣臉孔,五官,髮型的頭,緊閉著眼。
當下我只想回到床上,這必定是夢未醒。可是現實世界還有很多的工作等著我。
ㄧ面從眼角瞄著床底,確定那東西沒有任何變化,一面穿好衣服打點行李。懷著對牙膏的恐懼,拿了兩三顆口香糖便出門,連管狀的鞋油也不敢打開。
今天的工作ㄧ如往常,沒有異樣。只是接近中午時突然輕鬆了起來,心中不免開始胡思亂想。
到底是不是早上一時眼花呢。
是誰的惡作劇。
可以代替我上班多好。
趁著難得空閒,滿懷著難以壓抑的緊張,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一探究竟。
中午的陽光很強,但不刺眼。街上每張招牌,每位櫥窗人偶,都閃著金色的光芒,直到家裡每個角落。深吸口氣,推開房間的門。
床底下,已經有半個身體擠出來,露在外面。那雙手就抓在開口邊緣。
我彷彿聽見地板輕輕震動,以心跳的節奏。
它的形狀就像大型牙膏罐,只是蓋子不見了。裸露的鐵錫開口,飄散出的不是亮白薄菏味或三色彩虹,而是圓圓的黑色物體。近看,原來是一顆頭。一顆有著和我一模一樣臉孔,五官,髮型的頭,緊閉著眼。
當下我只想回到床上,這必定是夢未醒。可是現實世界還有很多的工作等著我。
ㄧ面從眼角瞄著床底,確定那東西沒有任何變化,一面穿好衣服打點行李。懷著對牙膏的恐懼,拿了兩三顆口香糖便出門,連管狀的鞋油也不敢打開。
今天的工作ㄧ如往常,沒有異樣。只是接近中午時突然輕鬆了起來,心中不免開始胡思亂想。
到底是不是早上一時眼花呢。
是誰的惡作劇。
可以代替我上班多好。
趁著難得空閒,滿懷著難以壓抑的緊張,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一探究竟。
中午的陽光很強,但不刺眼。街上每張招牌,每位櫥窗人偶,都閃著金色的光芒,直到家裡每個角落。深吸口氣,推開房間的門。
床底下,已經有半個身體擠出來,露在外面。那雙手就抓在開口邊緣。
我彷彿聽見地板輕輕震動,以心跳的節奏。
Thursday, December 07, 2006
沒有哪麼簡單就能快樂過生活的
夢061201
Sunday, November 26, 2006
夢061126
神仙們給每個人一個寵物。
我的是跟指頭一樣小的白狗,全身毛茸茸。
每個人拿到的時候都處在無生命的狀態,要由不同的方式喚醒。
當我正在想如何讓他活過來的時候,他就變成一隻褐色的狗,開始在我手上跑來跑去。
ㄧ抬頭剛好前面有個鏡子,我臉上長出了許多毛。
正在思索每天起床都要刮鬍子的時候就醒了。
我的是跟指頭一樣小的白狗,全身毛茸茸。
每個人拿到的時候都處在無生命的狀態,要由不同的方式喚醒。
當我正在想如何讓他活過來的時候,他就變成一隻褐色的狗,開始在我手上跑來跑去。
ㄧ抬頭剛好前面有個鏡子,我臉上長出了許多毛。
正在思索每天起床都要刮鬍子的時候就醒了。
Friday, November 24, 2006
三人樂團
Tuesday, October 31, 2006
月亮還記得(V.3)
月亮還記得1969年7月20日,太空人阿姆斯壯在攝影棚裡宣稱登陸月球的瞬間,她手上的茶杯也翻落了。
直到現在,那雙染漬的襪子仍然躺在衣櫃抽屜裡,除了三十年來的掛號信,這裡從沒響過一聲登陸的門鈴。電視機傳來的播報聲繼續前進著,茶漬在棉質細孔裡漫延,從那天起時間再也無力推動完整的她,月亮分裂成了兩半。
其中一半的她,繼續在軌道上繞著,守時,美麗,明亮,甚至帶來更多的遐想,另外一半,則逃離了時間,逃離了空間,沒有人看的見。
曾經她和阿姆斯壯維持著一個月見面一次的關係。阿姆斯壯愛慕著她,表現殷勤,口沫橫飛的述說航太工程師的無聊生活,那些程式和黃色笑話。確實他相當成功,有著不錯的收入,在太空熱潮中,他也被視為最有潛力。但是,月亮早已厭惡,她並不想成為反射著光芒的鏡子,也不喜歡冰冷的數字。最初他們在科學研習社認識,也只是因為那裝著冷氣的舒適課室,吸引怕熱的她加入。之後持續的關係,也不過是基於繞行生活軌道的習慣。拋物線,萬有引力定律,這些東西即使能帶給人類最大的進步,她也不看在眼裡。
她想成為繪畫的靈感,流浪者的歌頌,糕餅的雛形,革命的浪漫記憶。
於是在登陸的前一個月,她逐漸將自己抽離現有的生活。當阿姆斯壯發現她眼中已不再閃爍著一絲欣賞的光芒,而被無法理解的黑影所吞蝕,他便徹底的瘋了。
月亮沒有打算向世界揭發這場騙局。
她知道每月的匿名匯款,躲在暗處的便衣刑警,偽裝成紅綠燈的機器人,或是藏著攝影機的郵筒,都是阿姆斯壯的吩咐,像人造衛星一樣監視著她。
她知道要若無其事的生活著,刻意表現給閉路電視後方的他,這就是最直接的復仇手段。
阿姆斯壯派出了學者,畫家,詩人,以她為主題創作一篇篇作品,試圖激盪她的感性。資深演員喬裝的人們,並沒有誠實欣賞著美,尤其是假意拿著咖啡杯的半調子,只為等她露出一絲驚喜,那便是默認了他們再三排演的文藝氣氛,默認了這場戲。當夜裡那一張張憂愁的青春面孔仰望著她,傾訴著過度感性帶來的哀傷,她也只能對這些太早跟隨阿姆斯壯年輕人們,回報禮貌的憐憫。
月亮還記得太空人阿姆斯壯走下小艇時,面罩上所反射的日光燈影,和攝影棚的天花板。她繼續運行著,從未讓人發現一點異常。那消失的一半留在過去,與這場騙局,一起飄向宇宙深處,而盡責的一半,依舊規律繞行。
即使有天我們發現了真相,疑惑又驚訝的望著她,她也不會給予活在電視裡的人們,任何暗示。
她也只能對著你我,投以同樣的月光。
直到現在,那雙染漬的襪子仍然躺在衣櫃抽屜裡,除了三十年來的掛號信,這裡從沒響過一聲登陸的門鈴。電視機傳來的播報聲繼續前進著,茶漬在棉質細孔裡漫延,從那天起時間再也無力推動完整的她,月亮分裂成了兩半。
其中一半的她,繼續在軌道上繞著,守時,美麗,明亮,甚至帶來更多的遐想,另外一半,則逃離了時間,逃離了空間,沒有人看的見。
曾經她和阿姆斯壯維持著一個月見面一次的關係。阿姆斯壯愛慕著她,表現殷勤,口沫橫飛的述說航太工程師的無聊生活,那些程式和黃色笑話。確實他相當成功,有著不錯的收入,在太空熱潮中,他也被視為最有潛力。但是,月亮早已厭惡,她並不想成為反射著光芒的鏡子,也不喜歡冰冷的數字。最初他們在科學研習社認識,也只是因為那裝著冷氣的舒適課室,吸引怕熱的她加入。之後持續的關係,也不過是基於繞行生活軌道的習慣。拋物線,萬有引力定律,這些東西即使能帶給人類最大的進步,她也不看在眼裡。
她想成為繪畫的靈感,流浪者的歌頌,糕餅的雛形,革命的浪漫記憶。
於是在登陸的前一個月,她逐漸將自己抽離現有的生活。當阿姆斯壯發現她眼中已不再閃爍著一絲欣賞的光芒,而被無法理解的黑影所吞蝕,他便徹底的瘋了。
月亮沒有打算向世界揭發這場騙局。
她知道每月的匿名匯款,躲在暗處的便衣刑警,偽裝成紅綠燈的機器人,或是藏著攝影機的郵筒,都是阿姆斯壯的吩咐,像人造衛星一樣監視著她。
她知道要若無其事的生活著,刻意表現給閉路電視後方的他,這就是最直接的復仇手段。
阿姆斯壯派出了學者,畫家,詩人,以她為主題創作一篇篇作品,試圖激盪她的感性。資深演員喬裝的人們,並沒有誠實欣賞著美,尤其是假意拿著咖啡杯的半調子,只為等她露出一絲驚喜,那便是默認了他們再三排演的文藝氣氛,默認了這場戲。當夜裡那一張張憂愁的青春面孔仰望著她,傾訴著過度感性帶來的哀傷,她也只能對這些太早跟隨阿姆斯壯年輕人們,回報禮貌的憐憫。
月亮還記得太空人阿姆斯壯走下小艇時,面罩上所反射的日光燈影,和攝影棚的天花板。她繼續運行著,從未讓人發現一點異常。那消失的一半留在過去,與這場騙局,一起飄向宇宙深處,而盡責的一半,依舊規律繞行。
即使有天我們發現了真相,疑惑又驚訝的望著她,她也不會給予活在電視裡的人們,任何暗示。
她也只能對著你我,投以同樣的月光。
Sunday, October 29, 2006
夢061029
又再度穿上了高中的運動服,在教室裡和同學聊天等著老師來上課。
面孔們換成了大學同學,黑板上是數學算式。
趁著空檔去上廁所,經過其他間教室,心理跟自己說,我比他們大不只5歲呢。
要踏上樓梯的時候,老師正走下來。
面孔們換成了大學同學,黑板上是數學算式。
趁著空檔去上廁所,經過其他間教室,心理跟自己說,我比他們大不只5歲呢。
要踏上樓梯的時候,老師正走下來。
Monday, October 23, 2006
黯綠手指
又一次
卡在指甲縫裡的
失落感
記得離上次剪它不久
再多肥皂泡
也溶不化
那一顆種子
與它張牙舞爪的根
深深刺入赤裸裸指甲床
直到心臟
吸收著
ㄧ同搏動的記憶
長出新芽
再度持刀
將慘綠枝葉
蒼白盔甲
ㄧ同卸下
只是那血液中飄動的
根
日漸漫長
卡在指甲縫裡的
失落感
記得離上次剪它不久
再多肥皂泡
也溶不化
那一顆種子
與它張牙舞爪的根
深深刺入赤裸裸指甲床
直到心臟
吸收著
ㄧ同搏動的記憶
長出新芽
再度持刀
將慘綠枝葉
蒼白盔甲
ㄧ同卸下
只是那血液中飄動的
根
日漸漫長
邀請
雖然做音樂和寫東西是為了快樂,但創作者們多少會有需要被肯定的時刻,那樣的快樂是另一種收穫感。
譬如:"你好,我們是某某單位,對你的音樂很有興趣。"這樣的信件,就會讓人徹底高興起來。當然我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往往是做好的音樂,趕忙上傳到網路空間,強迫和幾個朋友分享。
能夠在現實世界或網路世界中,搜尋著創作者,輕易操縱他們情緒的調查員們,真是有著無上的權力。就好像時尚派對總有ㄧ群人可以決定哪些名流能夠收到邀請卡。當然許多時候我們仍然是繼續的沒沒無聞,畢竟在這個世界上同樣創作著的人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要是有一天我們也成為訂定標準的人,是否也會隨時留意下一個巨星?
到了那個地步,誰要來肯定我呢。那必定使人發慌。
譬如:"你好,我們是某某單位,對你的音樂很有興趣。"這樣的信件,就會讓人徹底高興起來。當然我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往往是做好的音樂,趕忙上傳到網路空間,強迫和幾個朋友分享。
能夠在現實世界或網路世界中,搜尋著創作者,輕易操縱他們情緒的調查員們,真是有著無上的權力。就好像時尚派對總有ㄧ群人可以決定哪些名流能夠收到邀請卡。當然許多時候我們仍然是繼續的沒沒無聞,畢竟在這個世界上同樣創作著的人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要是有一天我們也成為訂定標準的人,是否也會隨時留意下一個巨星?
到了那個地步,誰要來肯定我呢。那必定使人發慌。
Sunday, October 22, 2006
elephant eyelash-why?
有些樂團其實只有一個人,聽起來卻像是一大堆人。幹這種掛狗頭賣牛肉的事,elephant eyelash就是個代表。
簡單的剪剪貼貼,蠢蛋一般的手寫曲目,憑封面挑CD的人應該會忽略了它,大概一個創作天才又加上設計天才也太困難了。放來聽聽看吧,馬上就會對他粗糙手繪帶來的刻板印象完全改觀。ㄧ個人和自己做音樂,就好像寫日記ㄧ樣,總是容易繞著固定的語法字詞打轉。於是臥室出產的音樂,總有著千篇一率的自閉感,手上的材料不脫家裡冰箱。elephant eyelash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自己跟自己合唱,彈吉他打鼓加上合成器,材料從各式各地摘來,甚至連雙喉音都出現了,每首歌都錄上了好幾軌,空間中充滿了豐富的聲音,有源源不絕的靈感,一個男孩能夠這麼有耐心又細膩,唱歌又好聽,實在讓人懷疑。
Sand dollars,這首歌堪稱為溫馨主打,有著第一秒就抓住耳朵的前奏,緊接著是深具親和力的動聽吉他旋律,若是在電台播放ㄧ定成為大紅牌。當然不只這樣,鋼琴、貝斯、合聲、咚咚咚的鼓,不甘寂寞的在前奏喊著著one, two, three, four,中間有go, go, go!,真是幹勁十足的一首歌。
聽著他唱歌的聲音,我想他十分知道如何快樂的做想做的事情,並且完全靠自己。
簡單的剪剪貼貼,蠢蛋一般的手寫曲目,憑封面挑CD的人應該會忽略了它,大概一個創作天才又加上設計天才也太困難了。放來聽聽看吧,馬上就會對他粗糙手繪帶來的刻板印象完全改觀。ㄧ個人和自己做音樂,就好像寫日記ㄧ樣,總是容易繞著固定的語法字詞打轉。於是臥室出產的音樂,總有著千篇一率的自閉感,手上的材料不脫家裡冰箱。elephant eyelash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自己跟自己合唱,彈吉他打鼓加上合成器,材料從各式各地摘來,甚至連雙喉音都出現了,每首歌都錄上了好幾軌,空間中充滿了豐富的聲音,有源源不絕的靈感,一個男孩能夠這麼有耐心又細膩,唱歌又好聽,實在讓人懷疑。
Sand dollars,這首歌堪稱為溫馨主打,有著第一秒就抓住耳朵的前奏,緊接著是深具親和力的動聽吉他旋律,若是在電台播放ㄧ定成為大紅牌。當然不只這樣,鋼琴、貝斯、合聲、咚咚咚的鼓,不甘寂寞的在前奏喊著著one, two, three, four,中間有go, go, go!,真是幹勁十足的一首歌。
聽著他唱歌的聲音,我想他十分知道如何快樂的做想做的事情,並且完全靠自己。
Sunday, October 15, 2006
流水帳的翻案
曾經我也不喜歡blog或bbs上的流水帳,首先它通常會演變為情感充沛的有感而發,而我能看到的不外乎是認識的人,任意看見他們的深沉告白,把自己赤裸裸的解剖,連周邊的親朋好友師長仇敵也寫進來,這樣深交實在是有壓力的一件事情。再來是文章本身多少有著預設的讀者,對方或許是親密愛人,或許是尋覓中的徵友,或許就是他自己內心不為人知的一面。當不小心闖入這樣的對話空間,實在有種想看搞笑片,進場卻變成文藝片的感覺。最後或許是大家的生活類似,抱怨也類似,最後的心得也類似,看來看去常大同小異。
但假使今天是一偶像,有名氣的人,流水帳就變成了至寶,最好是越詳細越好。許多名人把一天的行程記錄下來,去過的地方馬上變成景點,看過的書馬上大賣。能窺見他們不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一面,又能成為日常生活的話題,實在讓人點了一篇又ㄧ篇。
當然,或許認識的某人以後成為超級掌權者,那麼他現在的這些流水帳馬上可以裝訂出書。不過即使我們也那麼的平凡,流水帳還是有著重要性,繼續寫下去也沒問題。那是因為當我們有能力跳脫的時候,這就是一桶最大且有效的冷水,告訴我們自己曾經多麼的鑽牛角尖,畫地自限,而在這暢快的灌頂之後,就能快速的邁向成仙之路。
因此我們該給所有的流水帳一些掌聲。
但假使今天是一偶像,有名氣的人,流水帳就變成了至寶,最好是越詳細越好。許多名人把一天的行程記錄下來,去過的地方馬上變成景點,看過的書馬上大賣。能窺見他們不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一面,又能成為日常生活的話題,實在讓人點了一篇又ㄧ篇。
當然,或許認識的某人以後成為超級掌權者,那麼他現在的這些流水帳馬上可以裝訂出書。不過即使我們也那麼的平凡,流水帳還是有著重要性,繼續寫下去也沒問題。那是因為當我們有能力跳脫的時候,這就是一桶最大且有效的冷水,告訴我們自己曾經多麼的鑽牛角尖,畫地自限,而在這暢快的灌頂之後,就能快速的邁向成仙之路。
因此我們該給所有的流水帳一些掌聲。
月亮還記得(1)
月亮還記得1969年7月20日,太空人阿姆斯壯在攝影棚裡宣稱登陸月球的瞬間,那時她手上的茶杯翻落了。直到現在,那雙染漬的襪子依然躺在衣櫃抽屜裡,除了三十年來的掛號信,這裡從來沒響過一聲登陸的門鈴。
茶漬在棉質的襪子上延展,直到無法抵抗細孔拉引而停留在黃與白的分界線,電視機的聲音仍然繼續前進著。從那天起時間也無力推動完整的她,月亮分裂成了兩半。其中一半的她,繼續在軌道上繞著,守時,美麗,明亮,甚至帶來更多的遐想。另外一半,則逃離了時間,逃離了空間,沒有人看的見。
月亮沒有打算向世界透漏這個秘密,原本她是非常氣憤的。這並不是因為每月匿名匯入的高額生活費,也不是因為躲在暗處像人造衛星一般監視著她的那些便衣刑警,偽裝成紅綠燈的機器人,或是裝著攝影機的郵筒。她知道那必定是阿姆斯壯的吩咐,每一樣都躲不過她的眼睛。她知道要若無其事的生活著,刻意表現給閉路電視後方的他,這就是最直接的復仇手段。
登陸以前,她和阿姆斯壯維持著一個月見一次面的關係。阿姆斯壯愛慕著她,表現殷勤,口沫橫飛的講述著航太工程師的無聊生活,那些程式和黃色笑話。確實他相當成功,有著不錯的收入,在太空熱潮中,他也是被視為最有突破力的。
但是,月亮早已厭惡,她並不想成為反射著光芒的鏡子,也不喜歡冰冷的數字。最初他們在科學研習社認識,也只是因為那舒適裝著冷氣的課室,吸引怕熱的她加入。之後持續的關係,也不過是基於繞行著生活軌道的習慣。拋物線軌道,重力定律,這些東西即使能帶給人類最大的進步,她也不看在眼裡。
她想成為繪畫的靈感,流浪者的歌頌,糕餅的雛形,革命的浪漫記憶。。
於是在登陸的前一個月,她逐漸將自己抽離現有的生活。當阿姆斯壯發現她眼中已不再閃爍著一絲欣賞的光芒,而被無法理解的黑影所吞蝕,他便徹底的瘋了。
茶漬在棉質的襪子上延展,直到無法抵抗細孔拉引而停留在黃與白的分界線,電視機的聲音仍然繼續前進著。從那天起時間也無力推動完整的她,月亮分裂成了兩半。其中一半的她,繼續在軌道上繞著,守時,美麗,明亮,甚至帶來更多的遐想。另外一半,則逃離了時間,逃離了空間,沒有人看的見。
月亮沒有打算向世界透漏這個秘密,原本她是非常氣憤的。這並不是因為每月匿名匯入的高額生活費,也不是因為躲在暗處像人造衛星一般監視著她的那些便衣刑警,偽裝成紅綠燈的機器人,或是裝著攝影機的郵筒。她知道那必定是阿姆斯壯的吩咐,每一樣都躲不過她的眼睛。她知道要若無其事的生活著,刻意表現給閉路電視後方的他,這就是最直接的復仇手段。
登陸以前,她和阿姆斯壯維持著一個月見一次面的關係。阿姆斯壯愛慕著她,表現殷勤,口沫橫飛的講述著航太工程師的無聊生活,那些程式和黃色笑話。確實他相當成功,有著不錯的收入,在太空熱潮中,他也是被視為最有突破力的。
但是,月亮早已厭惡,她並不想成為反射著光芒的鏡子,也不喜歡冰冷的數字。最初他們在科學研習社認識,也只是因為那舒適裝著冷氣的課室,吸引怕熱的她加入。之後持續的關係,也不過是基於繞行著生活軌道的習慣。拋物線軌道,重力定律,這些東西即使能帶給人類最大的進步,她也不看在眼裡。
她想成為繪畫的靈感,流浪者的歌頌,糕餅的雛形,革命的浪漫記憶。。
於是在登陸的前一個月,她逐漸將自己抽離現有的生活。當阿姆斯壯發現她眼中已不再閃爍著一絲欣賞的光芒,而被無法理解的黑影所吞蝕,他便徹底的瘋了。
Saturday, October 14, 2006
夢20061014,釘鎚
這是間相當老的醫院,有著木製的藥櫃和發黃的病歷紙。
有一位護理長,發給我們木柄釘槌。鐵質的,一端很尖銳,一端很鈍。
她說,這是從16世紀留傳下來的放血工具,你們都要自己嘗試看看。
同學們紛紛脫下了鞋襪,拿著鎚子往自己的腳筋敲去。
其中有個同學大喊:SMASH! 這幾個字像是漫畫ㄧ樣浮現在空中。
只剩下我還沒有敲,於是我醒了。
有一位護理長,發給我們木柄釘槌。鐵質的,一端很尖銳,一端很鈍。
她說,這是從16世紀留傳下來的放血工具,你們都要自己嘗試看看。
同學們紛紛脫下了鞋襪,拿著鎚子往自己的腳筋敲去。
其中有個同學大喊:SMASH! 這幾個字像是漫畫ㄧ樣浮現在空中。
只剩下我還沒有敲,於是我醒了。
Tuesday, October 10, 2006
dial-revenge
dial-revenge,高中時很喜歡聽,恰好昨天又聽到了,很懷念。
簡單來說,它就是在一面唸著書,一面不小心聽到時,會讓你在心裡說:幹,是這首歌,並且一直倒帶著回想著最開始聽著它的日子們,那樣子的歌。
到底是因為在青春時期聽到,深深的紀錄在成長裡,才造成這樣的衝動,還是歌曲本身的暗示,實在分不清楚了。
原文歌詞
Arbed amser ar ben fy hun
Cynal cof ac atgofion blin
Pwyth am bwyth
Chwant am chwant
A pob tro dwi'n codi'r ffon
Mae'n dweud 'Dial'
Dial anweddus
Nid grym arswydus
Aur, suth a mur
Tonfedd sur a chalon o ddur
Adeiladu ffiniau eglur
Newlid tonfedd
Nofio'r don
Dal yr abwyd nerth dy ben
Cwyd l'r wyneb
Dial anweddus
Nid grym arswydus
Aur, suth a mur
英文翻譯歌詞
Spending time on my own
Hold a memory and bitter recollections
Switch for switch, lust for lust
And each time I answer the phone
It says "revenge"
Indecent revenge, not a terrible power
Gold, frankincense and myrrh
A sour wavelength and a heart of steel
Building clear boundaries
Changing wavelength, swimming the wave
Hold the bait with all your might
Rise to the surface
Indecent revenge, not a terrible power
Gold, frankincense and myrrh
簡單來說,它就是在一面唸著書,一面不小心聽到時,會讓你在心裡說:幹,是這首歌,並且一直倒帶著回想著最開始聽著它的日子們,那樣子的歌。
到底是因為在青春時期聽到,深深的紀錄在成長裡,才造成這樣的衝動,還是歌曲本身的暗示,實在分不清楚了。
原文歌詞
Arbed amser ar ben fy hun
Cynal cof ac atgofion blin
Pwyth am bwyth
Chwant am chwant
A pob tro dwi'n codi'r ffon
Mae'n dweud 'Dial'
Dial anweddus
Nid grym arswydus
Aur, suth a mur
Tonfedd sur a chalon o ddur
Adeiladu ffiniau eglur
Newlid tonfedd
Nofio'r don
Dal yr abwyd nerth dy ben
Cwyd l'r wyneb
Dial anweddus
Nid grym arswydus
Aur, suth a mur
英文翻譯歌詞
Spending time on my own
Hold a memory and bitter recollections
Switch for switch, lust for lust
And each time I answer the phone
It says "revenge"
Indecent revenge, not a terrible power
Gold, frankincense and myrrh
A sour wavelength and a heart of steel
Building clear boundaries
Changing wavelength, swimming the wave
Hold the bait with all your might
Rise to the surface
Indecent revenge, not a terrible power
Gold, frankincense and myrrh
禁帶外食
抱歉
拿著照相機的
大師們
今天只開放
攜劍入場
這裡有
按摩浴缸
綠格線稿紙
公車站
也有
網路線
電梯指示燈
團隊會議
雖然無形
握著它,無須擔心
上回或許是
幼稚園
傳給鄰座女生
大學聯考
應徵工作
這回
想施展
三段式進擊
雙面轉換
一招斃命
任選
對手,獎盃
請自備
拿著照相機的
大師們
今天只開放
攜劍入場
這裡有
按摩浴缸
綠格線稿紙
公車站
也有
網路線
電梯指示燈
團隊會議
雖然無形
握著它,無須擔心
上回或許是
幼稚園
傳給鄰座女生
大學聯考
應徵工作
這回
想施展
三段式進擊
雙面轉換
一招斃命
任選
對手,獎盃
請自備
Saturday, October 07, 2006
流浪之歌
陽光走窗子進來
 這個房間剛好沒有開燈,像旅客一樣的我們正準備離開,迎接著難得的陽光,更加的難得。不曉得有多少電影,小說,散文,詩,畫,在討論著窗內與外,窺看者在怎樣的狀態,看待著怎樣的風景,又怎樣的被窺看,藉由這個通口跨過牆壁的阻礙,達到各種角度的連結。
這個房間剛好沒有開燈,像旅客一樣的我們正準備離開,迎接著難得的陽光,更加的難得。不曉得有多少電影,小說,散文,詩,畫,在討論著窗內與外,窺看者在怎樣的狀態,看待著怎樣的風景,又怎樣的被窺看,藉由這個通口跨過牆壁的阻礙,達到各種角度的連結。不論如何,這個畫面是定格了,但是時間仍不停的走著。照片紀錄的總是過去,卻永遠有現在的意義。
假使這是一間休息室,手中有著鑰匙,能夠在空間上達到盡情的隔絕,只剩下這樣一個明亮。而隱身於網路某條線路,坐擁著書房或圖書館或網咖的片刻,安全地面對電腦螢幕的窗的你我,不也是在空間上有著自主權,窺看著窗外的窗外。
那麼陽光是不是也穿透了窗和窗,照亮你的眼呢。
夢20061007
在手機響起,按下通話鍵的一刻,身後的地面卻變成了泳池。心裡想著千萬別掉下去,卻有如情節必要一般,以慢動作的姿態跌入水中。
手機在水中下沉,螢幕上同步顯示著文字,像字幕一樣。對方像語音留言一樣的講著話,想要打斷,嘴裡充滿了水只能發出咕嚕嚕的聲音。奮力往上游直到離開水面的瞬間,通話也結束了。
手機在水中下沉,螢幕上同步顯示著文字,像字幕一樣。對方像語音留言一樣的講著話,想要打斷,嘴裡充滿了水只能發出咕嚕嚕的聲音。奮力往上游直到離開水面的瞬間,通話也結束了。
無心吃蔔蔔成花

想要在友人造訪自宅時,展現生活情趣的一面,而想當個綠手指嗎?
不用選漂亮的花盆,昂貴的種子,煩惱怎樣的肥料最適當,擔心引來多少昆蟲蠅蛾,買哪一本植物栽種大全,在花市裡貨比三家。對於喜新厭舊沒耐心的現代人,這些只是浪費。
看,超市裡最便宜的紅蘿蔔,不必刻意澆水,隨意丟在室外,昂揚的綠意,就從保鮮膜掙脫向上了。比起動不動就枯萎的盆栽,這多能激勵生命的鬥志。原本要被切碎,悶煮,加上青豆,拌入番茄,或是在不消化的狀態進入馬桶,這樣悲慘的宿命,哪是霸在書桌陽台,被終日呵護的盆栽貴族所能了解。現在,它超脫了命運,超脫了寶麗龍盒的界限,整個陽台,整個大地,都是它的根基。看看它的綠葉,直挺挺的站著,努力吸收來自果實的養份,太陽的能量,珍惜著天命,直到養份消失的一天。枯萎了,超市還有的買。
當然,這樣紅中長綠的場景,對於很多的人來說應該是相當避諱,而失去了欣賞的機會吧。
dog on the counter
Thursday, October 05, 2006
freeze track
越來越少的字

不曉得有多少同學們開始習慣說:這就是"routine",又不能"skip"掉,好像一種傳染病似的。中英夾雜或許是顛覆傳統語言用法的一種,只是我覺得很難聽。特別是任何"○○"掉。精神科參考書-DSM IV中文版序裡,作者提到了這種參雜情形,希望自己的書能夠避免,而閱讀此書的讀者們也能好好想想。只是,實際看看大部分人,都已經嚴重的染上這種說話模式,尤其是難以規勸的一群。為了和他們講話,不得不自己也夾雜幾句英文,尤其是不必要的動詞。當然,說出"○○掉"這種話,我是絕對不幹的。另一個不喜歡的是:這個檢查是"for"什麼?乍聽之下會產生許多誤會。在這樣的模式下,講話斷斷續續,甚至連聽力也受到了影響,需要更多的話才能夠表情達意,似乎無藥可救了。
或許是因為忙碌,人情間短暫的交集,大多數人對話的方式,都是互相把語句丟到面前的空間,在自說自話的過程中讓語句自行互動,最後達到禮貌性的時間長度後就轉身離去,留下孤單的聲音,對方的個性、價值觀,都一片模糊。只是真實的話語,卻又因為總有傷人的危險性,在這樣情面至上的領域並不太受歡迎。對話以外,很多其他的部份,也慢慢的開始萎縮消失。內外夾攻之下,每個人講話的模式也逐漸同步。
最後我們唯一熟悉的語文模式大概就是病歷了,而且是充滿錯誤拼字文法和貧乏詞彙的病例。
爸爸常跟我說一個人一天有固定說話的量,多於它則回家就很沉默,少於它則聒噪。暑假的時候天天陪爸爸散步,十分了解這一點。只是漂浮在人情面上的話語,該無奈的記在帳上嗎。
Wednesday, October 04, 2006
小小天堂
靜音塞子
Tuesday, October 03, 2006
短章困境
我實在無法想像寫很長的文章是什麼樣子,或許這是一種天生的缺陷吧。以往投稿的文學獎,也只能寫到四千字左右,再往下寫就像是吃到飽的最後幾片肉或金針菇,已無法分辨好壞,因此只參加過散文組和新詩組。
越長的文章,越容易失去組織性。就像是煮四個人的菜和四百人的菜相比,除非是老練的辦桌師傅,後者很容易有太酸的糖醋魚,沒入味的滷肉等等。青年們常在個人暱稱、簽名檔等地方發揮文學創意,接觸的是報紙的標題和貧乏的內文,訓練的是條列式的問題回答方法,需要寫長篇心得的時候往往令人頭痛。身處在這個時代,我應該也適用以上的藉口吧。
當然青年們也有很多的心事,或是有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必要。只是從頭說起的同時,筆下往往變成了流水帳式的記錄。對比於一般營養不良的狀況,這樣富含情緒的記載文學,常能連載。
好好的描述情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些詞彙很可能還存在於沒看過的書上。而對於生活單調重覆,課業沉重的青年們,要有特別的記載素材,必須細心的體察。資訊過剩的時代,越來越多人已完成我們想做的事情,要在茂盛的樹枝上畫一片漂亮的綠葉,並不容易。
假使不願意屈服的話,就把這看作是磨練吧。從短篇開始也好。
越長的文章,越容易失去組織性。就像是煮四個人的菜和四百人的菜相比,除非是老練的辦桌師傅,後者很容易有太酸的糖醋魚,沒入味的滷肉等等。青年們常在個人暱稱、簽名檔等地方發揮文學創意,接觸的是報紙的標題和貧乏的內文,訓練的是條列式的問題回答方法,需要寫長篇心得的時候往往令人頭痛。身處在這個時代,我應該也適用以上的藉口吧。
當然青年們也有很多的心事,或是有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必要。只是從頭說起的同時,筆下往往變成了流水帳式的記錄。對比於一般營養不良的狀況,這樣富含情緒的記載文學,常能連載。
好好的描述情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些詞彙很可能還存在於沒看過的書上。而對於生活單調重覆,課業沉重的青年們,要有特別的記載素材,必須細心的體察。資訊過剩的時代,越來越多人已完成我們想做的事情,要在茂盛的樹枝上畫一片漂亮的綠葉,並不容易。
假使不願意屈服的話,就把這看作是磨練吧。從短篇開始也好。
開電腦船,渡電子海

依賴網路而生的我們,開著一艘艘電腦小船,每天在資訊海中載浮載沉,捕撈一天的所需,對著空白的聲納發呆,等待渡船經過。
各式各樣的船隻,有著暱稱、顯示圖片等個人訊息構成的無形船板,在廣大的海上航行。對於自命為酷的族群,這不止是個天堂,也是疲於奔命的迴圈。暱稱之外還要有個人訊息,發布的文章標題不能太平凡,收聽的音樂會顯示在公眾之海上,往往調整這一切後,又發現迎面而來的是更光鮮亮麗的船,不只早有自己所有,更上一層樓。
在海上航行往往是孤單的,即使網站下方的計數器告訴你,正有幾百幾千艘船航行過這裡。看見一艘有趣的船,發出電子訊號,留下浮標,往往像是投往黑暗的海底深處,慢慢遠去。或許是太多人發出電子訊號,接收器已經超載了。
唯一可以保證快速回應的,大概是電子賣場的老闆吧。
不論為了什麼,在這一個航程上,終究會有人在更高的浪頭,有人將要滅頂。每天變換的船身也開始變成每週變換,每月變換,最後開始尋找自動變換的程式。
而我們只能看管好儀表板,繼續前進。
各式各樣的船隻,有著暱稱、顯示圖片等個人訊息構成的無形船板,在廣大的海上航行。對於自命為酷的族群,這不止是個天堂,也是疲於奔命的迴圈。暱稱之外還要有個人訊息,發布的文章標題不能太平凡,收聽的音樂會顯示在公眾之海上,往往調整這一切後,又發現迎面而來的是更光鮮亮麗的船,不只早有自己所有,更上一層樓。
在海上航行往往是孤單的,即使網站下方的計數器告訴你,正有幾百幾千艘船航行過這裡。看見一艘有趣的船,發出電子訊號,留下浮標,往往像是投往黑暗的海底深處,慢慢遠去。或許是太多人發出電子訊號,接收器已經超載了。
唯一可以保證快速回應的,大概是電子賣場的老闆吧。
不論為了什麼,在這一個航程上,終究會有人在更高的浪頭,有人將要滅頂。每天變換的船身也開始變成每週變換,每月變換,最後開始尋找自動變換的程式。
而我們只能看管好儀表板,繼續前進。
Friday, September 22, 2006
Textbook of Drug Abuse
soulwax和電子音樂的血脈連結,也可從他們一支向藥物文化致敬的音樂錄影帶中了解。當然這支影帶是被許多國家禁播的。e-talking,從A到Z所有的藥物都出現了,不管是三環類抗憂鬱藥、血清素回收抑制劑、鎮定安眠類藥物、鴉片類藥物、躁鬱症使用的鋰鹽等等,讓外行人知道不是只有搖頭丸一種藥,也讓內行人大感溫馨。
當然,藥物濫用是不合法的,別輕易嘗試。
Textbook of Stage Move
音樂表演,除了甩動長髮與腳踏節拍以外,還能有什麼舞台動作嗎?
Soulwax,這群拿著laptop,合成器,貝斯,猛力敲打真鼓的過動兒們,用現場表演告訴你,光是按電腦上的鍵盤,都可以很有帥勁。不管是搖頭晃腦的舞客,還是兩手交叉胸前的文藝青年,都會被這種強而有力的動感催眠。這樣廣大的渲染力,不光是因為混合了電子音樂與搖滾,他們身體裡長的就是跳舞細胞,編曲不必堆疊醞釀,樂句必定科技酷帥,各種電子聲響構成樂曲的主體。當然,光是節拍只能驅動身體,無法更深層感染性靈。他們的搖滾旋律和煽動性十足的唱腔,樂在其中的舞台動作,讓台下聽眾清一色忙著甩頭跳躍和拍手。
簡單來說,這不是給人家坐著聽的音樂,是要跳著聽的。
混合電子音樂和傳統搖滾三件式樂器的創作,已經成為潮流一陣子了。第一類來自搖滾樂團的轉型,加入鼓機、合成器或打碟機,第二類來自個人樂手自行錄製樂器和電子音樂的部份,再進行混音,包括電腦音樂家。第三類則由電子樂手與傳統搖滾樂手合組的團體。在第一類中,我心目中的代表者是supercar,這個已經解散的經典日本樂團。流行音樂中也有許多加入了DJ的樂團,多是走向nu-metal。
soulwax或許比較偏第三類。難得的是,在加入了電子節拍的競爭狀態下,鼓手的角色仍然相當有存在感,令人激賞。尤其在整體舞台效果上,有鼓手敲打真鼓,能帶來完全不同的立體感。當然,使用靜態性樂器(包括合成器、laptop等)的樂手,能在盯著螢幕手指以外跟隨節拍搖擺,也是強大渲染力不可或缺的因素。最後一個讓台下潰堤的是結合聽眾指揮者和歌唱的主唱,有時拿起麥克風吼叫牽動聽眾的情緒,有如party中的DJ,有時又回到歌曲之中。
不論是任何一種控制樂器的樂手,都容易陷身在自我的情緒中,而有不同的舞臺動作,例如瞪靴一派的電腦音樂家在台上高興的玩弄laptop,不必和台下有眼神交會,慢慢的堆疊各種小聲響,台下也自在的閉著眼睛輕鬆享受,進入另一個意境神遊。不同的音樂就會影響不同的舞台表現,重點還是回歸到音樂本身。假使要soulwax帶著毛帽搬沙發到舞台上排排坐玩電腦,台下的聽眾大概會馬上把手邊的藥全吞了吧。
Soulwax,這群拿著laptop,合成器,貝斯,猛力敲打真鼓的過動兒們,用現場表演告訴你,光是按電腦上的鍵盤,都可以很有帥勁。不管是搖頭晃腦的舞客,還是兩手交叉胸前的文藝青年,都會被這種強而有力的動感催眠。這樣廣大的渲染力,不光是因為混合了電子音樂與搖滾,他們身體裡長的就是跳舞細胞,編曲不必堆疊醞釀,樂句必定科技酷帥,各種電子聲響構成樂曲的主體。當然,光是節拍只能驅動身體,無法更深層感染性靈。他們的搖滾旋律和煽動性十足的唱腔,樂在其中的舞台動作,讓台下聽眾清一色忙著甩頭跳躍和拍手。
簡單來說,這不是給人家坐著聽的音樂,是要跳著聽的。
混合電子音樂和傳統搖滾三件式樂器的創作,已經成為潮流一陣子了。第一類來自搖滾樂團的轉型,加入鼓機、合成器或打碟機,第二類來自個人樂手自行錄製樂器和電子音樂的部份,再進行混音,包括電腦音樂家。第三類則由電子樂手與傳統搖滾樂手合組的團體。在第一類中,我心目中的代表者是supercar,這個已經解散的經典日本樂團。流行音樂中也有許多加入了DJ的樂團,多是走向nu-metal。
soulwax或許比較偏第三類。難得的是,在加入了電子節拍的競爭狀態下,鼓手的角色仍然相當有存在感,令人激賞。尤其在整體舞台效果上,有鼓手敲打真鼓,能帶來完全不同的立體感。當然,使用靜態性樂器(包括合成器、laptop等)的樂手,能在盯著螢幕手指以外跟隨節拍搖擺,也是強大渲染力不可或缺的因素。最後一個讓台下潰堤的是結合聽眾指揮者和歌唱的主唱,有時拿起麥克風吼叫牽動聽眾的情緒,有如party中的DJ,有時又回到歌曲之中。
不論是任何一種控制樂器的樂手,都容易陷身在自我的情緒中,而有不同的舞臺動作,例如瞪靴一派的電腦音樂家在台上高興的玩弄laptop,不必和台下有眼神交會,慢慢的堆疊各種小聲響,台下也自在的閉著眼睛輕鬆享受,進入另一個意境神遊。不同的音樂就會影響不同的舞台表現,重點還是回歸到音樂本身。假使要soulwax帶著毛帽搬沙發到舞台上排排坐玩電腦,台下的聽眾大概會馬上把手邊的藥全吞了吧。
Thursday, September 21, 2006
夜間的背景音樂
每天晚上洗完澡,一邊擦乾頭髮,一邊聽音樂打混,真是最奢侈的享受了。有人比喻說,夜晚與白天就像河的兩岸,睡覺的時刻就是在渡河。假使如此,往渡船頭的腳步也不能太急躁,船才能使得穩。即使有許多的考試和作業要處理,仍然要有喜歡的事情,撫平一天與另一天之間的粗糙地帶。睜開眼睛就開始工作,工作直到閉上眼睛,這樣的生活會讓靈魂重心不穩,慢慢的傾斜了,甚至吃水越來越深。當然,最好是靠岸後還能到船上再待一會。
這幾天陪伴我度過短暫悠閒時光的是這首歌:fly me to the moon,相信許多人早已耳熟能詳,不論在視覺或聽覺上都非常適合夜晚的歌。從google上找到的資料,原作詞曲者是Bart Howard,於1954年所做,之後經過改編,被太多太多人的翻唱,包括法蘭克辛納屈、納京高等等。我聽的版本是由Julie London所演唱的爵士版本,隨性又深情的嗓音,搭配弦樂及鋼琴、爵士鼓,非常有廣闊的空間感,更加適合夜晚。
以下為歌詞: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life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hope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一首歌傳唱許久,不僅本身是個經典作品,也是現在人的幸運。
一個晚上能夠悠閒一會,行船平穩,更是福氣。
Wednesday, September 20, 2006
夢060920
這次是要看精神科急診,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學長跟我說不用緊張,有什麼不舒服都說出來。
場面跳到了中正紀念堂,許多人把國父的照片高高掛上寶藍色的屋瓦。
有些巨大的穿著軍裝的人偶,從階梯上翻滾下來。黑頭車停在廣場。
我站上某個講台,跟台下說,有這麼多時間可以在這裡鬧事,不如多去幫助別人。
場面又回到診間,放了很多種食物,每樣食物都有四五份。有青菜,豆干,蛋。
醫師在旁邊笑笑的看著我,跟我說不用客氣。當我伸手拿起某一樣,他就開始紀錄。
我不禁猶豫了起來。
很短的夢,不怎麼精彩。
學長跟我說不用緊張,有什麼不舒服都說出來。
場面跳到了中正紀念堂,許多人把國父的照片高高掛上寶藍色的屋瓦。
有些巨大的穿著軍裝的人偶,從階梯上翻滾下來。黑頭車停在廣場。
我站上某個講台,跟台下說,有這麼多時間可以在這裡鬧事,不如多去幫助別人。
場面又回到診間,放了很多種食物,每樣食物都有四五份。有青菜,豆干,蛋。
醫師在旁邊笑笑的看著我,跟我說不用客氣。當我伸手拿起某一樣,他就開始紀錄。
我不禁猶豫了起來。
很短的夢,不怎麼精彩。
Tuesday, September 19, 2006
油墨味
會在書店裡翻開這本書,純粹是被這麼長的書名吸引。原本以為這是封底的副標題,而最後兩個字,又被旁邊擺放的書陰影擋住。因為先天薄弱,就要活在別人的陰影下,這樣悲慘的人間故事,怎麼可以發生在空靈的書本世界呢。基於關懷弱者的心理,又好奇最後兩個字究竟是什麼,所以把書拿起來看。
一看才發現,原來以為是封底的竟然就是封面,以為是副標題的就是書名。
把書拿起來,不等於把書打開,相信長年專攻陷阱設計的出版社老狐狸們,都深諳這個道理。有時候掉進陷阱裡,發現裡面沒有什麼奇景,便爬出來回家了。而馮光遠先生的這本書,安置了一個無厘頭的玩笑,是讓我在書店裡站著翻完的動力。或許有些人會說這個玩笑很後現代,我只能說好笑的事情,有一個定律,就是千萬不能說,一方面是說了就不新鮮了,另一方面是不說才能吊胃口。所以就自己去發現吧。
閱讀這本書,有種久未體會的讀報快樂。最近的報紙都過於單調,對於每日從事單調工作的現代人,好像我們的社會就是這麼的單調。而這本書正是以時事為核心,再次回顧和解讀,產生許多有趣的推演。整本書看似戲謔,看似嘲諷,對比於血腥恐怖的報紙,該算是個輕鬆小品。
現實世界常常是殘酷的,想要把這些事情轉化為引人興趣的材料,至少要有敏銳的社會觀察力,親身的歷練,充沛的想像力或聯想力,以及生活的態度,不斷的在外界與自我間來回溝通。許多人都相當熱衷這樣的寫作,畢竟時事就是最切身的材料,把現實世界寫的十分有趣,感覺就是個生活藝術大師,生活品味大師。只是,往往在成功暢銷之前,自己就先面對生活的困難,於是生活手札也變成了心情置物箱,甚至垃圾箱。
更深一層,加入理想的期待,參雜生命的體會等等,比較抽象、嚴肅,但也是作者本身特色的展現。
在這方面,西西先生就是最了不起的典範。
蝴蝶效應
今天有一通電話,說要找林小姐。
對方相當客氣,我也禮貌的說,抱歉,這裡只有林先生歐。
問了電話號碼,竟然沒錯。
隨口問了問這個電話的來源,原來是某位在忠孝東路四段看診的醫師,
到某家礦泉水公司看了某樣產品,留下的電話。
對方問我認不認識這位醫師。
我跟她說,雖然我剛好也姓林,剛好是見習醫師,但我不認識那位林醫師。
這位小姐又苦惱又高興的說,怎麼會這麼可愛呢?
打錯的電話很有趣。
明明素不相識,似乎接起電話的人,總是和想要找的人有著命運的關連。
有時連自己也好奇起來,到底那位神秘客是誰呢。
雖然這是一通打錯的電話,卻讓人不想直接掛斷。
尤其到樓梯間接電話的時候,還碰見了可愛的人呢。
對方相當客氣,我也禮貌的說,抱歉,這裡只有林先生歐。
問了電話號碼,竟然沒錯。
隨口問了問這個電話的來源,原來是某位在忠孝東路四段看診的醫師,
到某家礦泉水公司看了某樣產品,留下的電話。
對方問我認不認識這位醫師。
我跟她說,雖然我剛好也姓林,剛好是見習醫師,但我不認識那位林醫師。
這位小姐又苦惱又高興的說,怎麼會這麼可愛呢?
打錯的電話很有趣。
明明素不相識,似乎接起電話的人,總是和想要找的人有著命運的關連。
有時連自己也好奇起來,到底那位神秘客是誰呢。
雖然這是一通打錯的電話,卻讓人不想直接掛斷。
尤其到樓梯間接電話的時候,還碰見了可愛的人呢。
Monday, September 18, 2006
Bye Bye Pacifier
如果要在世界上找出一種表情,來詮釋滿足的感覺,大概非吃奶嘴莫屬了吧。
這個禮拜在兒童心智科見習,徹底見識到奶嘴的威力。雖然爸媽都嫌它很臭,每次出門卻絕不能忘記帶,當小朋友怎麼哄都不會聽的時候,還有個最後的手段。
許多爸媽都稱呼奶嘴為嘴追。嘴追都有個蓋蓋,不用時可以蓋起來,以免小朋友吃到髒東西。光是跟小朋友說,給你吃嘴追好不好,小朋友馬上跟著魔了一樣,開始露出非常期盼的眼神,表現出極度配合的態度。這時候爸媽就可以很壞的盡情吊胃口,強迫他們說拔拔拜託,麻麻拜託,我會乖乖等等。
等到開始戒除奶嘴的時刻,就要和小朋友明定規矩,只能吃半小時就拿走。這時看到小朋友意猶未盡的表情,用盡各種方法想要搶回奶嘴,真是不忍又好可愛。
今天有位小朋友,太過喜愛它的嘴追,而來看門診。媽媽很困擾,小朋友找嘴追比找媽媽還勤。
醫師說,可以在出門前和小朋友一起把嘴追放在桌上,跟嘴追說掰掰。
假使小朋友哭鬧,跟他說嘴追今天在家,自己要乖。
這樣的場景相當適合出現在麥兜故事系列,最好奶嘴上再添一支揮動的手。
青春期延長的我們,有沒有跟嘴追掰掰呢。
這個禮拜在兒童心智科見習,徹底見識到奶嘴的威力。雖然爸媽都嫌它很臭,每次出門卻絕不能忘記帶,當小朋友怎麼哄都不會聽的時候,還有個最後的手段。
許多爸媽都稱呼奶嘴為嘴追。嘴追都有個蓋蓋,不用時可以蓋起來,以免小朋友吃到髒東西。光是跟小朋友說,給你吃嘴追好不好,小朋友馬上跟著魔了一樣,開始露出非常期盼的眼神,表現出極度配合的態度。這時候爸媽就可以很壞的盡情吊胃口,強迫他們說拔拔拜託,麻麻拜託,我會乖乖等等。
等到開始戒除奶嘴的時刻,就要和小朋友明定規矩,只能吃半小時就拿走。這時看到小朋友意猶未盡的表情,用盡各種方法想要搶回奶嘴,真是不忍又好可愛。
今天有位小朋友,太過喜愛它的嘴追,而來看門診。媽媽很困擾,小朋友找嘴追比找媽媽還勤。
醫師說,可以在出門前和小朋友一起把嘴追放在桌上,跟嘴追說掰掰。
假使小朋友哭鬧,跟他說嘴追今天在家,自己要乖。
這樣的場景相當適合出現在麥兜故事系列,最好奶嘴上再添一支揮動的手。
青春期延長的我們,有沒有跟嘴追掰掰呢。
Sunday, September 17, 2006
新鮮老百姓與星光大道

當大學生們剛脫離下午起床的糜爛生活,叫苦連天的適應開學時,還留戀於青春美好的校園生活的我們,已經完成第一周的見習生活。第一周來到的是精神科慢性病房,又稱為希望之家。整層樓只有這區開始使用,其它部分都還在裝潢中,希望之家的木牌,懸在這空曠的空間。這裡的病人狀況,不至於太難控制,又還未康復到可以出院,恰好介於中間。希望之家,也可說是復健之家。形形色色的人物,與伴唱機、跑步機、保護室、會談室,構成了慢性病房的場景。
當然,病人偶爾還是會有暴力行為、對其他病人不友善,而被關進保護室。風平浪靜的時候,病人的生活非常規律,有著各種活動,甚至還有些忙碌。往往想找病人談話,都會被回以:我沒空。還有一間空的病房,搬來幾張桌椅,給我們當作休息室。只是從護理站到休息室的走廊,往往有許多病人拉著我們報告昨天晚上沒睡好,老公沒來探望,賣了哪件衣服給誰穿,短短一段路,都要走個十分鐘,好像星光大道上的明星一樣,有接受不完的訪問。也就是上圖紅色的部份。
最後一天,我和19歲的小病人道別,跟她說下禮拜就換別的醫師,要好好照顧自己。她笑著跟我說:恩!
暫時忽略她的各種妄想症狀,真是純真的19歲。
Saturday, September 09, 2006
夢060909,家庭夢旅行
這是一場夢境,主角是我的家人。
第一個景點是長庚大學的管理大樓中庭,不知何時成為觀光客的集散地,還有小型的雙人電動車來來去去。家人把行李放好準備要出去吃飯,我想起忘了拿皮包。回去時碰上了一位高瘦的男同學,旁邊的電視機傳來"重播第十五次時,打開某扇門會獲得幸運"的聲音,恰好鑰匙在我手上,這時還剩下五次。同學和我一起等在門的旁邊,穿著十分整齊。
每重播一次的畫面都只有少許類似,或許是片頭曲,或許是字幕裡的幾個字,要非常仔細看。終於到了第十五次,我迅速把鑰匙插入有著怪物臉的鎖孔。門開了,外面停了一台計程車,同學突然頭暈倒地,呢喃的說,幸運不能平分。
回到了家人身邊,時間已經相當晚。想尋找某個認識的朋友留宿,她是個會英文與俄羅斯語的日本人,綽號巫婆,我們卻忘了地址,一間一間的找。終於有扇門開了,兩個穿著和服的婆婆招待我們進去。我一面用英文問她們認不認識巫婆,一面用中文要我爸不要亂動她們家的東西。她們用日語交談好一陣,向我搖頭表示不認識這個人,突然她們兩個蹦出中文對我爸說,沒關係阿。我問她們為何不一開始就用中文,她們卻不回答。這時我哥也已經在浴室裡洗澡了。
巫婆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幾乎是這個民宿區的賣點。我實在很懷疑她們會不知情,又故意裝聽不懂中文。我一面偷偷的把東西收好,一面跟我哥說洗好澡就直接往外跑。這時我故意的把手伸到床底下,跟她們說,巫婆其實在這裡吧。她們臉色馬上大變,開始把電話線等等都切斷。我們家人都往外跑。結果我的手機不見了。
馬路上開過來幾台車,上面寫著司法。我朝他們揮手,他們卻視而不見的開走了。剛才那間房子理的家具,都裝了滑輪,一樣樣的從房子裡滑出來,直直的向著海。我心想原來要湮滅證據了。心生怒意,就和不知那來的幾個忍者,回去揍了她們一頓。
後半部分不知道我媽跑去那,結果就醒了。
第一個景點是長庚大學的管理大樓中庭,不知何時成為觀光客的集散地,還有小型的雙人電動車來來去去。家人把行李放好準備要出去吃飯,我想起忘了拿皮包。回去時碰上了一位高瘦的男同學,旁邊的電視機傳來"重播第十五次時,打開某扇門會獲得幸運"的聲音,恰好鑰匙在我手上,這時還剩下五次。同學和我一起等在門的旁邊,穿著十分整齊。
每重播一次的畫面都只有少許類似,或許是片頭曲,或許是字幕裡的幾個字,要非常仔細看。終於到了第十五次,我迅速把鑰匙插入有著怪物臉的鎖孔。門開了,外面停了一台計程車,同學突然頭暈倒地,呢喃的說,幸運不能平分。
回到了家人身邊,時間已經相當晚。想尋找某個認識的朋友留宿,她是個會英文與俄羅斯語的日本人,綽號巫婆,我們卻忘了地址,一間一間的找。終於有扇門開了,兩個穿著和服的婆婆招待我們進去。我一面用英文問她們認不認識巫婆,一面用中文要我爸不要亂動她們家的東西。她們用日語交談好一陣,向我搖頭表示不認識這個人,突然她們兩個蹦出中文對我爸說,沒關係阿。我問她們為何不一開始就用中文,她們卻不回答。這時我哥也已經在浴室裡洗澡了。
巫婆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幾乎是這個民宿區的賣點。我實在很懷疑她們會不知情,又故意裝聽不懂中文。我一面偷偷的把東西收好,一面跟我哥說洗好澡就直接往外跑。這時我故意的把手伸到床底下,跟她們說,巫婆其實在這裡吧。她們臉色馬上大變,開始把電話線等等都切斷。我們家人都往外跑。結果我的手機不見了。
馬路上開過來幾台車,上面寫著司法。我朝他們揮手,他們卻視而不見的開走了。剛才那間房子理的家具,都裝了滑輪,一樣樣的從房子裡滑出來,直直的向著海。我心想原來要湮滅證據了。心生怒意,就和不知那來的幾個忍者,回去揍了她們一頓。
後半部分不知道我媽跑去那,結果就醒了。
USB
Friday, September 08, 2006
近來可好
往往開學一個月,會想要回頭看一看,然後為這學期卜卦,安排計畫,但這怪異的課程,實在不是一般的卦象。所以這學期仍然在未知的狀態。共筆與投影片的惡戰也過去了,投影片多到離譜的狀態時,已經脫離老師的控制,反而有種解脫的感覺,好像旁觀一個人在亂七八糟的房間找東西的場景,每個抽屜都放一堆東西,開了只好關起來。當然我們都知道他是找不到的。時間到,大家開始吵鬧,也就可以下課了。
地下室的空氣總讓我覺得充滿輻射,即使它是種看不見的東西,但是上課時常飄來的溶劑或煙味,莫名震動的天花板,或是過高的出席率,都讓我覺得一定有輻射。我真心的想建議學校,可以把教室蓋在頂樓,有窗戶,雖然不一定會有鳥兒飛過,至少天快黑的時候可以提醒老師下課。政大以前有個老師都喜歡在6,7點上課,也就是天快黑的時候。天黑了,當然要快點讓同學回家,這樣才安全。
這個時刻,許多以前的同學已經開始步入社會,當兵,研究所。不論受到多少社會來的考驗,一個接一個的我們都要成為大人。當然我知道我們都已成年。不過也難以否認,黃金般的少年歲月,總是難以割捨,而使青春期過度的延長。但,假使跳過了大人的味道,直接面對更後面的一些東西,好像更可惜。
或許是那一點保養品的氣味,不想喪失的理想,有如胃酸般嚥下的生活酸苦,一個開朗的嘴角,和一點不礙事的眼淚。
或許更快,或許更簡單。
地下室的空氣總讓我覺得充滿輻射,即使它是種看不見的東西,但是上課時常飄來的溶劑或煙味,莫名震動的天花板,或是過高的出席率,都讓我覺得一定有輻射。我真心的想建議學校,可以把教室蓋在頂樓,有窗戶,雖然不一定會有鳥兒飛過,至少天快黑的時候可以提醒老師下課。政大以前有個老師都喜歡在6,7點上課,也就是天快黑的時候。天黑了,當然要快點讓同學回家,這樣才安全。
這個時刻,許多以前的同學已經開始步入社會,當兵,研究所。不論受到多少社會來的考驗,一個接一個的我們都要成為大人。當然我知道我們都已成年。不過也難以否認,黃金般的少年歲月,總是難以割捨,而使青春期過度的延長。但,假使跳過了大人的味道,直接面對更後面的一些東西,好像更可惜。
或許是那一點保養品的氣味,不想喪失的理想,有如胃酸般嚥下的生活酸苦,一個開朗的嘴角,和一點不礙事的眼淚。
或許更快,或許更簡單。
Tuesday, September 05, 2006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